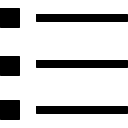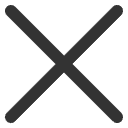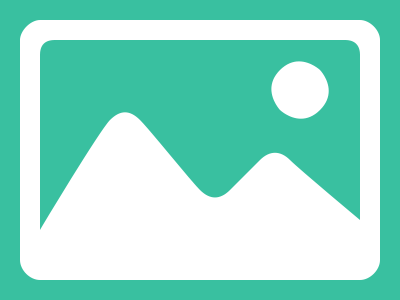靖康奇耻
《大宋英雄传》系列小说
第三部
朱升
《靖康奇耻》15
第15回
黑心肠坏人先告状 昧良心恶毒害好人
玉启与美银正当妙处,有人推门进来,以为是老五回来了,玉启吓得从美银身上滚了下来,一手抓住衣裤,跳下床来,打算夺门而出。当他发现,破坏他们好事的竟是陆承耀,他怒从心底起,一挥手,给呆若木鸡的陆承耀两个耳光,打得承耀眼冒金星。
陆承耀这个年纪轻轻尚未见过女人的光棍汉,见了这挡子事儿,是既羡慕,又自认倒霉。人们
。因为,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自留地只有使用权,没有所有权。我的那块“自留地”就是我的那个“中一”(4)班(此时,中学由六年制改为四年制,不分初高中,统称“中”),我是班主任。我的“自留地”何止被别人染指,乃至被人任意践踏、摧残,我也无可奈何,因为,“所有权”不在我手中。
我19岁高中毕业后,开始了从当农业中学教师起步,以后干过小学、初中,乃至职业高中,这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,我当了37年的班主任,教两班语文,最后三年之所以没当班主任,是因为我实在力不从心,学校党支部书记才饶了我,让我享了三年的“清福”。
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吧,文化大革命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,我所在的“戴帽子”东风小学中学部正式与东风小学脱钩,成立了市属东风中学,从此,我开始了中学教学生涯。学校只有“中一”、“中二”两个年级,总共12个班,500人左右,之后,我被新来的金书记任命为中一(4)班班主任,还兼任学校理论组副组长(书记是正组长)。我从教一生,从没当过“长”,理论组副组长是干什么的,我也不太清楚。
“就是写文章啊,你没看到报纸上常刊豋有分量的‘一评、二评’等等文章吗?” 金书记事后这么对我说。
我暗自一笑:那些文章是有背景的,事出有因的,一介平民何足挂齿,风马牛不相及的!这书记也太天真了一些,准确的说,他的心大了一些,不过,人无大志不发,马无夜草不肥!
学校正式开学不久就开进了“工宣队”,我诧异,这学校地处郊区,四周都是农村,离市区远,开进个“贫宣队”还差不多,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呗,怎么开进个工宣队的?
“我们学校呗,直属市教育局领导,不受公社管,你怕还不知道吧,公社书记是正团级,中学书记也是正团级,他们怎领导得了我们?”书记说,“我在校领导小组会议上已作出决定,学校要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,下农村工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,你当副队长,正队长由团支部书记、行政秘书小陆担任。”
“我,我怎么当得了,一不会唱,二不会跳──” 我知道,一旦成立了文艺小分队,会没日没夜地到处跑,我妈身体并不好,需要照顾,特别是晚上,我有意推辞。
“不要你唱,也不用你去跳,你去拉手风琴。”
倒也是,学校那48贝司的手风琴我倒是能拉响的,只是不会用贝司和声,只能打打拍子而已。
经过一番紧张的动员挑选和排练,学生中会跳,会唱,会拉二胡、吹笛子的,大约凑齐了20来人男女队伍,文艺宣传小分队算是正式成立了。再接着,这支小分队开进了各个工厂。
一段时间后我问书记:“这班上耽误下来的课怎么办?”
“演出多数是在晚上,你白天抓紧一点。是学习文化知识重要,还是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重要?这个你要弄清。” 书记是军人出身,做事历来雷厉风行,不容讨价还价。
“行!反正是开卷考试,又没人来检查你,管它呢。” 我暗自想。
每到工厂演出,工厂倒是挺客气的,每人发两个实心馒头慰劳,倒也省了我那每月28斤口粮计划。
也就这么过了一个多月吧,学校调来位矮矮的、头顶秃光了的陈天龙老师,五十出头了吧(我猜想),是个教代数的,书记一询问好不高兴,原因是他会拉二胡,还听说他代数教得特好,可惜不教我班代数,我倒有点儿遗憾。再接着,学校调进位体育老师,姓徐,叫徐德升,这位徐老师人还没到我校,臭名声到扬开了,说他特郎当,快30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,没件像样的衣服,整天是球衫球裤,每月的35块5毛不够他抽香烟,就改抽水烟,每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,和着衣服就睡觉,“哪像个老师?”金书记可不高兴了。
当这位徐老师来到后不久,看看这个非常简陋的中学居然还有只手风琴,倒也迷上了,没过两个礼拜,他的手风琴拉得比我好多了。我想,徐老师年轻,手指灵活,我老了。
“书记,我妈手指胳膊有关节炎,天冷了,常发作,需要照顾她生活起居,我老婆又在外地工作,家中没人能照顾她,我想,这小分队手风琴就让小徐去拉吧?”
“不行!”
“为什么?”
“他年轻,光棍一条,宣传队女生多,演出又常常在夜里,防着点。”
我心想,人家光棍一条,就算看上个女生又何尝不可?我上中学时,就有好几位老师找的老婆就是自己的学生。在书记面前,我也没敢多说什么,书记参加过抗美援朝,上过战场,响当当的革命派,他的话代表党,我只好早点回家安顿好妈躺下,拦在小分队演出前赶到演出现场。
这一学期,学校陆陆续续调进了不少老师。
第二学期一开学,书记在大会上宣布学校要勤工俭学了,为的是要增加学校收入,干什么活儿呢?
“是办校办厂,还是进工厂学工?” 我知道去工厂学工,工厂多多少少也能给点钱的。
“都不是,在学校里搓泥丸。” 书记在喇叭里这么说。
“搓泥丸做什么,那玩意儿常常是小孩子的恶作剧?”
“告诉大家,我们这里地下发现埋藏着大量的石油,这泥丸儿是打深井用的,需要量很大,价钱也很高,我们不花成本,只花功夫……” 书记兴致勃勃。
这一个个如乒乓球大小的泥丸儿,遇上水不就化了吗?到底作何用途,没人能说清楚。书记在作息时间上作了调整,每天上午上四节课,下午全体师生参加搓泥丸。没过一个星期,每个教室后都堆满了泥巴和搓好晒干的泥丸。所幸的是,学生搓起泥丸儿来倒很内行,速度快,因为附近有家砖瓦厂,制砖和搓泥丸过程差不多,不少学生家长都在砖瓦厂工作,很多学生都会做。
一天下午,那郎当的体育徐老师来到现场参加搓泥丸,一会儿后他高声朗诵:“……五岭逶迤腾细浪,乌蒙磅礴走泥丸……” 读后,哈哈大笑,很多人也跟着笑了,书记听后却紧绷着个脸。看看书记那脸色,我顿觉不安……果不其然,书记立即在小黑板上写了通知:“今晚在饭堂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,不得请假,不得缺席!!!” 这后面的三个感叹号,令人胆战心惊。
学校饭堂并不大,连同锅灶和一个教室差不多吧,布置得却庄严肃穆,第一个被批判的是饭堂小师傅,人称“小白麻子”的。白麻子是饭菜大师傅从县区带来的徒弟,他脸上有几粒白麻子,要不仔细看还感觉不到。小白麻子的罪行是,他不光偷吃偷拿,还偷饭菜票,转手卖给在校吃中午饭的学生,这案子是学生检举出来的,学校早做了准备要整一整他,批判后的结果当然是开除,不,准确的说应该叫辞退,他不是正式工。
底下该轮到体育徐老师做检査了,只见他走到主席台前,深深向主席像鞠了三躬,背诵了一段语录,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拿出张纸:
“最高指示──”
我趴在饭桌上闭上眼睛。我知道,就是这位徐老师,曾参加过省运动会七项全能比赛,他曾在学校体育场上轻松地越过了一米八的横杆,他是个体育人才啊,如今……
“吴老师!”
我吃了一惊,马上振作精神站立了起来,等待书记的发落。
“你,你看看徐老师检查得深刻不深刻,能不能过关?”
“啊,啊,这,这个嘛,我看呢,还可以吧,其实,其实,小徐老师是不懂诗的,他是个教体育的呗,那诗里的乌蒙,是山的名字,红军,红军过乌蒙山,把乌蒙山当小泥丸儿,主席诗,大气磅礴,我,我们搓泥丸,倒要学学,红军,过那山,藐视困难的精神……”
“哈哈……”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海笑。
“照你这么说,小徐说的主席两句诗,倒起了鼓干劲的作用了?”
“啊,这,这个嘛,小徐主观上可能没这层意思,客观上到起了这个作用,我是这么理解的,不知对不对。”
一阵沉默,让人难受。
“有不同看法吗?有,站起来说说,没关系的,我们既不揪辫子,也不打棍子。”
还是一阵沉默。
“没有话说就散会。”
会场上一阵骚动,叽叽呱呱说个不停。 坐我旁边的一位外语女老师,在我臂膀上打了一拳,笑弯了腰。
“你怎么啦,无缘无故打我干什么?”
“下面,学校请大家吃面疙瘩,放开肚子吃,不收钱,也不收粮票,这是伙食结余,大家放心吃。” 书记又一次讲话,转移了我的目标视线。
“这伙房,怎么看,总觉得它不像伙食房,倒像洗衣房,洗得肚子里没有一点儿油水……”
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狂笑!
按规定,学校公共食堂每月应该有计划猪肉供应,猪肉去哪里了呢?还不是让书记招待了客人,大家敢怒不敢言,只好“迂回作战”。
有人走了,有人在等待,我去了趟厕所,小徐老师也跟着来了,在往回走的路上,小徐老师拔出一根烟给了我,紧紧握了握我的手,两眼泪汪汪的,从此以后,我俩成了要好的朋友,尽管我岁数比他大得多。
两个月以后,钻井队不要泥丸儿了,这每一个教室后面堆满了的泥丸儿怎么处理呢?书记根本就没有作指示,我估计,他大概疲劳了,“全世界都对不起我!”这是他此刻的心态。我又想,自从办了这学校后,倒轰轰烈烈做了不少事,结果如何呢?一场空,它和轰轰烈烈的文革一样,是由无数个毫无意义的元素堆积起来的。此后,每到放学,学生们口袋里的泥丸总是装得满满的,去做什么呢?打树上的鸟,去果园里打树上的桃子,有的还伤了人,结果呢,一只鸟也没打到,空喜欢一场,这又给班主任带来不少麻烦事。
学校上课又重新走上正轨,一次,当我快走到教室,听到教室里乱成一团,一个劲地齐声喊道,“上床!上床……” 我火气直冒,在讲台前站着,班长喊了声“起立!”
“不许坐下,说!什么上床上床?”
四十二个学生没一个开口!
“班长,你说,这上床什么意思?” 我拿起教鞭,走到班长前指着她鼻子问。
“我,我,我也不懂。”
班长是位女生,白净净的,文文雅雅的,她哭了,我心到一软。我在讲台前来走了几个来回,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熊,同学们等待我的发落。
“坐下吧,现在上课!”
下课后我沉重地坐在办公室里连抽两支闷烟,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,心想利用课间操时间再去问问班长吧,班长内向,胆子小,估计再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的,免得节外生枝,问了其他班委,班委们摇摇头,都说“不知道!”就这么过了不到一星期,班上秩序倒也平静了不少,没再听到起哄的闹声。接着,教我班的代数老师来了。
“吴老师,不好意思,我要请三天病假,印了几张卷子,我的代数课就让同学们做作业吧,你照应点,落下的课,以后补。”
“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──”
“不,开刀,开痔疮。”
“行,三天恐怕不行吧,那就多休息几天好了,你这代数课我来上,教哪里啦?”
我说这话是有把握的,我是个高中毕业生,教初中代数还不是小菜一碟?更何况我在外地还干过:“校长兼校工,烧饭带打钟” 呢,我什么课都上过。
“对了,想起来了,与你同轨的那位教代数的陈天龙老师去哪儿了,好多天不见他人了?” 我明白了我班代数老师为什么要把课改成自习,没代数老师为他代课。
数学老师摇摇头。
又过了一星期,班上有两位女同学一下子停了三天课,问了好几位同学,几乎一模一样回答“不知道!”
我翻了翻同学们的花名册,知道了两个停学女生住址。
“黄燕人呢?怎么不来上学的?” 我找到了停学女生黄燕的家。
“啊,你是学校老师啊,她,她回我老家了。”
我听后倒吃了一惊,才知道黄燕的母亲不是本地人,她一口里下河口音。
“她户口不在本地,是借读我校的?”
“不,在本地,农村户口,她舅舅病了,回我娘家代看看的。”
什么原因也没问出来,又去了另一女生家,却吃了个闭门羹,我气极了,两位女生成缋是不错的,我是痛失“爱生”啊!我把这情况向金书记汇报了,书记倒显得很淡然。
“你尽到责任就算了,这青春期的女孩子的事是不好多管的。”
我听后心想,这上学与青春期不青春期的有什么关系啊,他并不知道,这年龄段的男男女女学生正处于叛逆期呀,一足失,千古恨,书记真是个当兵的料!
学期临近结束,暑假即将到来,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,那个教代数的陈天龙被宣布正式逮捕!
“书记,陈天龙老师为什么被捕?”
“啊,这个嘛,听说是与一张反动传单有牵连,这事发生在他海门工作期间,与我们学校没关系。”
“没关系?书记,你仔细点儿,听说,姓陈的常在家里替学生补代数,多数还是女生,我们这些学生只是十五六岁呀,是未成年人啊,听说,我们班上就有女生在他家补过课。”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,不会的,他孙子都快要上中学了。”书记笑笑。
新学期刚开始,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,那个一向惹书记讨厌的体育老师徐徳升居然被调进省级中学工作,这可不容易啊!而金书记本人被免职回到省中接受审查!我听到消息后既开心又伤心,伤心的是我失掉了一个好朋友徐德升,开心的是那个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的书记也有今天下场!我想啊,这人生就像一碗菜,有保鲜期,金书记的那碗“菜”大概已到期了。我又想起句名言,“有爱人和自爱能力的人,才能支撑起他的精神世界,工作起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”,那位姓金的书记,缺少的就是爱人和自爱精神。他排斥异己,急功近利,又背着个参加过“抗美援朝”的沉重的金子招牌,太多的名利欲望变成一块石头,最终砸了自己的脚。
我立即去问新调来的孙书记。
“文化大革命算是正式结束了,一切要拨乱反正,徐德升老师是个被湮没的体育人才,他之所以衣冠不整,这与他教体育有很大关系,一个体育老师,总不能衣冠处处西装革履去上体育课吧,你说是不是?他父母离世早,兄弟俩和一个妹妹过日子,妹妹残疾,弟弟还是个徒工,兄弟俩工资低需要养活妹妹,所以他生活才拮据的。这次为了调他去省中教学,还闹了一番。”
“调就调呗,闹什么?”
“我用词不当,应该是‘争’。”
“谁和谁争?”
“省中和体校争啊,争着要他去。至于说到那位姓金的前任书记,你还记得有一位全国知名的数学家杨х吗?”
“知道,本市人,是省中走出去的。”
孙书记点点头,叹了一口气,说:“数学家杨х高中阶段的数学老师徐х夫是省中著名数学老师,可惜他自杀身亡。”
“为什么要自杀?”
“还能为什么?办他的学习班嘛,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,把一个中学数学老教师,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,这不是笑话吗?学习班上不让他睡觉,没日没夜的,那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就是姓金的,他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呀,参加过抗美援朝呗,有了政治资本呗,要不,他能当上你们学校的支部书记吗?算算他的学历,他连个高中都没上完,怎能进高中课堂?” 说着说着, 这位新来的孙书记涨红着脸,站了起来。
“你别忙走,” 孙书记抓住我胳膊,“听说,你的语文课上得很好,我心想让你向全市开一堂公开课──”
“不行不行,我们是乡下学校,哪能和城里学校相比呢,开这样的公开课,你这不是让我去献丑?”
孙书记笑笑说:“文化大革命结束前,你们学校曾经排了一个大合唱参加郊区比赛,还得了名次,有这么一回事吗?”
我点点头。
“那些诗是你朗诵的,对不对?”
我又点点头。
“那些诗还是你写的吧?你还是男声领唱?”
“那,那年五一劳动节,我在上海人民广场看到一场大合唱联想起来想试试的,我们学生识歌谱能力很差,调门五花八门,没办法,重唱和轮唱是分开进行练习的,然后再组合,否则,要‘打架’的, 至于写的诗,我是受到‘长征组歌’启发后写的,也没新的创意。”
“有了这两点就行了,我全力支持你上公开课,你需要什么我给什么,我来这学校工作的唯一目的,就是团结大家,从整体上提高教学质量,希望你带个好头,即使上失败了也不要紧。我知道,那姓金的在这里当家,开始时,他是看中你的,还让你当了理论组副组长,久而久之,发现你不好驾驭,于是改变了态度,你还记得那次加工资的事吗?符合条件有五人,只加4人,对不对?你差点没有加得成,是不是?”
我点点头:“他姓金的欺人太甚,算工龄我排第三,算工资水平,我最低,排第一,我只拿35块5,他姓金的工资是我的两倍还多,近八十块钱,他能加工资我为什么不能加?我犯了什么错误不能加,那时我们学校属郊区政府领导,才去了农工局反映的。”
“农工局接待你的姓陈的科长是我中学同学,我来之前特地走访了他,目的是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情况,是他告诉我的,为了你能加到工资,我的同学先后和姓金的吵了三次大架,拍桌子打板凳的,最后,你们学校一位姓顾的老师当了‘替死鬼’,对不对?”
我又点点头:“他也该加,不该加的是他书记本人。”
孙书记坐下,掏出一支烟给了我,说:“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,怎能自己拉帮结派呢?这不是乱了自己的阵脚吗?教学工作还能搞好?这是个常识问题。这下好了,他回到省中后只好坐冷板凳了。”
“省中那位自杀身亡的徐老师,就这么草草了事吗,不平反?”
“平什么反?又没谁给他下结论戴帽子。浩劫啊,一场浩劫!”
“这倒是。”
之后,我想,如果省中那位自杀的徐姓老教师的学生若不是著名数学家的话,结果又是如何呢?这人际关系呀,怎么说才好呢……
约过了两个星期吧,已在省中工作的徐德升老师特地来到我校找我,一见面,他狠狠抱了抱我,叫了声“大哥!”
“活得怎么样,还是那么吊儿郎当的?招人讨厌吗?” 我哈哈一笑,看看他身上衣著倒也干干净净。
“好多了,谢谢,妹妹进了绣品厂,自己能养活自己了,我兄弟俩如释重荷。”
“哎呀,我说小徐啊,你怎的不早告诉我一声的,我有个表哥在手工业管理局当副局长,让他安排你妹妹工作还不是一句话,你妹妹是个残疾人呗,那个绣品厂属手工业管理局领导,我表嫂就在那里工作。”
“我怎么知道呀。大哥啊,我终生不忘你啊,今天特地带来条自行车外胎送你,现在市场上买不到,我知道你那辆自行车内外胎补了又补,胶了又胶。”
“多少钱,说!”
“是次品,不值钱,正品买不到,我弟弟在橡胶厂工作,到底多少钱我也不知道!你要是给钱,就不像兄弟了。”
“那好,你等一会儿,我马上就到。”
我急急忙忙跑到校门口小店里,花了2块8毛买了一条“飞马”, 对小徐说:“这条‘飞马’值多少钱你是知道的,你就收下吧。”
“行行行。”
我俩聊了一阵子,因为要上自习课,小徐老师也就离开了。
这学期快要结束时,那位秃头老家伙陈天龙居然无罪释放!不过,学校并没安排他再去上课,而是安排他进了文印室,为什么不让他进课堂呢,这里面必有玄机,只是无法打听到准确消息。此后的一段时间,我发现陈天龙几乎不出门一步,老是呆在文印室里抽闷烟,一张蜡纸,没个三四天他是刻写不好的,他在混日子!
时光荏苒,光阴似箭,一晃几年过去了,学校党支部书记换了一任又一任。一次,家中劈柴斧子坏了,妈要我去铁工厂买把新斧子,妈说那斧子好用,是出口产品,我去了,想不到的事发生了,呆在销售科卖斧子的,正是当年我班那两个中途休学女生中的一个黄燕,她见了我,很不好意思,站了起来叫了一声。等她开了票,我给了钱,拿到货,她陪着我走出厂门,两人聊了一会儿。
“你怎么进了铁工厂的?这是个全民单位啊,能进去可不容易。”
“我是子女调换,我爸原是铁工厂的。”
“知道啦,你中途辍学是因为要进铁工厂?其实,你再等两年进去也不迟呀,到时,你就有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。”
“不是着急要进厂的。”
“那次,我去过你家──”
“知道,事后,我妈告诉过我,我不想再上下去了,我受不了,难不成老师一点不知道我停学的原因吗?”
我面对着那小河,河里脏兮兮的,什么东西都有,我想了一阵,突然转身问:“你去过陈天龙家补过课?”
黄燕闷声不响,当她再次抬起头面对着我时,满面泪水,我顿时明白了,也不想再追问下去了,转身想离开。
“畜生!畜生!畜生!” 我愤怒地把脚下一块石子儿狠狠踢进了河里。
黄燕哭得更厉害了:“老师,你,你是位好老师……”
“不,不对!我是个不称职的老师,我没保护好你俩,我失责!”
我向前走了几步,停下,反身向黄燕走来,问:“张玉英呢?” 张玉英是另一位“补课”女生。
“她,她死了,投江自杀的。”黄燕蹲在地上抱头痛哭。
“狗日的!天杀的!” 我拿地上一块半截砖头狠狠砸向河上桥墩,走了。
老家伙陈天龙快退休了,一次,我去文印室拿试卷,见文印室只小张一个人在。
“你老爸身体怎么样啊?” 小张能进学校工作是子女调换,他爸老张原是我校文印室的。
“谢谢吴老师关心,我爸挺好的,他常提起你。”
“是啊,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啦,从小学部开始就是同事,你爸那一手好字真叫人叫绝。对了,陈老头子去哪儿了?这几天一直没见他人,你恐怕要忙多了?”
“他来不来反正一个样,来了又不刻钢板,成天伏桌子上睡觉。”
“大概是晚上忙,欠睡吧!堤内损失堤外补,这是现代京剧中的一句话。”
我俩笑了一阵。
“陈老头儿这次损失够惨重的,补也补不起来了,他领养的那个儿子死了。”
“什么什么,你说清楚?” 我忙问。
原来,陈天龙先后有两任妻子,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下两儿一女,不久,他在海门又诱骗了一个比他小近20岁的漂亮女学生,方和前妻离了婚。谁知,第二任妻子自从打胎后再也没能怀上,于是领养了一个儿子。这个领养儿子长大成婚后,他又奸污了领养儿子的老婆,这就等同奸污儿媳,我们当地人叫“扒灰”,消息传开了,领养儿子觉得无脸见世人,于是自杀身亡!
“畜生!畜生!一刀阉割了它才好,让他去当太监!”
小张“咯咯”笑个不停。
我又问小张:“算算帐,他先后有两个老婆,还有三儿一女,他工资并不高,怎能养活他们?”
“听说,他以老婆的名义开了个烟店,常卖假烟、走私烟,一次被查出,罚了好几千。”
“那烟店还在经营?”
小张摇摇头说:“不知道。”
“一个人面兽心的东西,这是学校失职!” 我夹着一叠试卷愤愤走了。
若干年后我也退休了,因生源越来越少,我们原来的那个中学撤销了,退休的教职员工归另一个叫新港中学代管,新港中学对退休人员倒是挺客气照顾的,每年总要组织旅游,还发了不少东西,请吃请喝。一次重阳节前学校打电话通知,每一个退休人员都必须到校,不能乘车行走的要家属送,不得缺席,说有什么重要表格要填写,还要带身份证,是教师的,还要带“四证”。那天我骑电瓶车去了,一到学校,从一辆出租车里走出位老人,老人拄着有四只“脚”的拐杖,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挪。
“吴老师。”有人叫。
我看看四周,只有几个年轻人在打篮球,我一个都不认识,于是继续走。
“吴老师!”
这次喊声清清楚楚告诉我,是那位老人在叫。我马上走上去看了又看,从哪个面看我都不认识他。老人脸扭曲了,满脸寿斑,身子佝偻着,走起路来一步一挪。
“我是陈天龙。”
“啊,是你呀,我当是谁呢。你怎么不带个人来陪陪的呢?”
陈天龙摇摇头,似乎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样子,再也没能开口说句话,我也懒得理睬他,丢下他,快速进了学校阶梯教室,大家拿到了一张表格纸,过了会儿,讲台人说一句我们就填一格。表格很快填好了,离吃中饭还有点时间,大家聚一起闲扯,十来分钟后我们进了学校饭堂,没过多久,陈天龙居然坐我身旁来了,我真的很不愿意,见了他,恶心,饭都吃不下去。
“你是高级?”
“什么高级?”我从包里拿出张《参考消息》,心里想,他说话足够精炼的了。
“就是──职称。”
“副高。”我也精炼。
“你不是──中师生吗,怎评得上?”
“不对,我是高中生。” 我头也没抬一抬,懒得回答他。
“评,评职称,干嘛──要大专的。”
“学历是可以变的,把业余时间用在看点书上,不就解决问题了?” 我提高了嗓音。
陈天龙看看我,略略点了点头,又问:“拿多少钱?”
我先伸出左手拇指和食指,后张开右手四指。我真的很不愿意和他说话。
“教师中,我工资最低。”
我听后,放下报纸,看了他一阵,说:“你知道不知道教师上岗要有‘四证’,有了这四证才能称得上教师?”
陈天龙摇摇头,过了会儿问:“哪四证?”
“学历证书,上岗资格证书,职称证书,聘用证书,按照常规两年一聘用,你早已不是个教师了,你能拿到工资就已经不错了,自己保重吧,不要想得太多。”
陈天龙听后一声不吭,一会儿后他叹了口气说:“你说得,在理,我,时日,不多了。”
“这句话用在每个人身上都合适,秦始皇想长生不老,那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,结果还不是一场空?”
陈天龙点点头,说:“我和秦始皇,不同。”
“没有什么两样的,都是人嘛,看你路远迢迢,还能一个人乘出租车来到这里,已经不错了,家里就抽不出个人来陪陪?” 我眼睛盯着报纸问。
“他们,没良心的,我算,做了,一场梦。”
“你这梦做得挺不错的,一生做的都是美梦、春梦。”
“吴先生,你真会说话,不骗你,我得了癌症,已开始痛了。”
不知什么时候,见他拿出一个药瓶和矿泉水。
“不至于吧,什么癌呀?” 我翻开报纸骂了一句“尽是广告,没看头!”
“前列腺癌,不骗你,在上海查过。”
我一听,觉得好笑,骗我不骗我有什么关系,他活得够长的了,我倒希望他早点死掉才好,免得再殃及别人:“你那前列腺负荷太重了,超负荷,所以才得癌症的,暂且歇息,有朝一日卷土重来,孙思邈百岁还得子呢。”
“孙,孙,孙什么,住哪儿?”
我海笑了一阵,说:“别着急,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他的,前列腺癌有什么关系啊,一刀把它割了,还有精囊,同样派用处,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,不愁治不好它。”
陈天龙歇了一阵,看看我要离开,又忙说:“医院开的药,不管用,进口药,报销不了,偏方更贵,这四五千块钱一月不够用的。能不能请你认识的那个孙,孙什么的呢,开个药方呢?” 他似乎来了点精神。
我听后暗自一笑,他还在做他的美梦,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,还当什么教师?我突然又想起易卜生的话:“每一个生命都有责任,我们的过咎,不在于所为之恶,而在于未行之善。” 我不能同意他这样的看法,姓陈的所为之恶,还能不“在于”?我不光“在于”,还耿耿于怀呢!
“不错啦,要放在现在,法律制度完善了,你一分钱也拿不到,更别想享受医保了。面对死亡,你害怕了?你有没有想过,你践踏了我的自留地,摧残摧毁了我两朵美丽的花蕾,她俩是未成年人,是独立的生命个体,不是被玩弄的工具,你醒悟了吗?你内疚了吗……”
一阵连珠“火炮”放完,我快速来到厨房窗口拿起快餐盒,愤愤离他远远的。